铁路作家推荐之二:张力
分享到微信
×用微信“扫一扫”,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
即可将网页分享给您的微信好友或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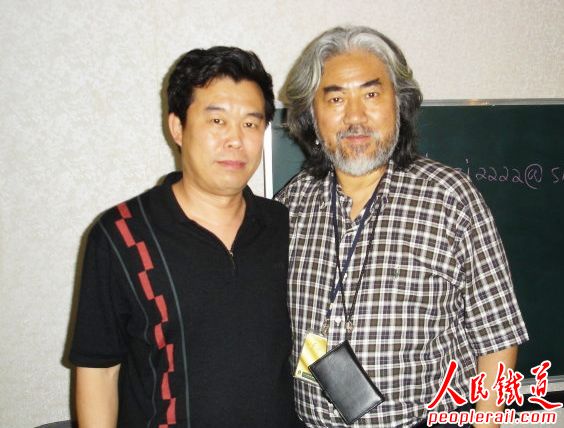
锦州市地处渤海湾--亦称锦州湾,蓝色的海洋与城内的紫荆山遥相呼应。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锦州人文环境独具风貌,人才荟萃。在辽宁省当代文坛,锦州市作 家方阵以其平民性的创作理想与实践,对于锦州市文化的掘进和提升,有着独特的品性与价值。锦州籍作家张力(笔名力歌)在生活潮涌中辛勤笔耕,进入文学城 20余年,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满腔热情地投入生活,高扬时代的主旋律。张力1988年开始写作,已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中国作家》、《十 月》等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300万字,《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曾选载中、短篇小说数篇,著有长篇小说《世纪大提速》、《大 案追踪》、《官殇》,短篇小说集《拥抱日出》、《歌厅里的格格》和纪实文学集《罪恶档案》等,荣获国内各种文学奖励十余次。中篇小说《大站》和短篇小说 《两个人的车站》分别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04年度中篇小说》和《2006年度短篇小说》。
青年时代的张力,认识了作家孙春平,自此张力开始了小说写作。他初期名为《小镇从容》的小说,一出世即获得了锦州市政府文学奖。这篇小说,不仅是张力 创作的真正起步,更隐伏了他的创作诉求和品性。可以说,他至今所有作品或主题或叙述或气质或精神或立场,都能在《小镇从容》中找到线索。小说的空间是小 镇,但重点却在普通百姓的普通情感之上。关注平民百姓,关注生活中普通人的心理,历来是张力平民情怀的焦点所在。对于作家张力,在创作的起步之时,就能够 如此明晰创作理想和内容,这样的自觉意识,是弥足珍贵的。
张力作品中主要有两个世界:一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世界,一个是铁路生活的世界,作家的创作具有这样两个资源,题材繁多,但其中的精神特质是相似相近的, 具有同样的指向,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执着与坚韧,营构出张力式的文学世界。在当代作家中,张力谦虚地说自己,搞文学是像园丁侍弄花草,张力是如此淡泊低调, 其作品又颇具分量的。
《大站》是张力小说境界走向厚重、深邃和高雅的足迹。
《大站》(载《上海小说》2004年2期,收《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4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中篇小说选》等)是相当够篇幅的一部中篇小 说,《大站》既是小说家形式选择之功,又不仅仅归功于小说的形式选择。《大站》没有写出够份的腐败分子,却透视了没有腐败分子在场的生活的腐变相,而且这 种腐变相是呈弥漫状态的。腐败分子是可恨的,生活的腐变则是可怕的。可怕在这种腐变正在作为一种基层生存“智慧”被使用着。社会还没有想出好办法来遏止 它,人们也还没有机会痛恨它。张力在《大站》里既描述了生活的腐变,也描述了人们对这种腐变的甚是普泛的暧昧态度。《大站》的沉实、厚重,对生活负真相进 行了批判,对人的正面性品质、正面性情感进行了真诚抒写。前者可以给人以思想上的惊醒,后者则能给人以情感上的感动。但当下的文学却总是跛着脚走路。虽然 广大文学阅读者总是不忘朝文学要感动,但文坛却总是单向度地追逐以姿态的“坏想象”所营造出来的没有感动的文学“尖锐和深刻”。这是现代主义传染给现实主 义的“文学精神病”。接受非理性思潮浸染的现代主义就是这样看世界:现实是非理性的、不可认识和无法解释的,现实是破碎的,现实是梦幻、荒谬与虚无,现实 是人的生存的尴尬处境;现代主义就是这样地摆弄揭示生活的一种弥漫性的负面真象,给人以警醒,这是《大站》的主题基调。但《大站》在完成这一文学主题时, 同时留住了与生活的负面真相对立着的生活的正面真实,亦即留住了与人的负面品质、负面情感相对立的人的正面品质、正面情感。这样,留住《大站》里的小说家 的激情,就不是偏狭、冷酷的那一种,而是内蕴着感人的爱意、能给人以精神温暖和感奋的那一种。应该承认小说《大站》的此种精神姿态,成就于对谭连民、杨启 才这两个小说人物的成功塑造。这是两个既有违规经历又有抗拒违规“智慧”的人物,作家张力就在这一点上保留了对自己笔下人物的良知。也就是凭这份良知,他 没给这两个人物涂抹肮脏的面孔,而是还以这两个人物该有的阳光。这样也就为《大站》这部中篇小说,保留了一份文学该有的感动。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就很感 人。他们是真正的“同志”加朋友。他们不争权夺利,不委琐,他们都很敬业,敢负责任,其至有献身精神。在许多小说和影视剧里看惯了头头们之间那种貌合神 离、相互整治、互设陷阱,再来体认《大站》里谭连民、杨启才两人的真诚相处,当然会倍觉亲切、舒服、爽悦,觉得就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像是心灵得到了某种慰 藉。他们可以惹出我们这样的憧憬:如果给他们一个非“无原则状态”的大环境,他们甚至会为社会做出伟人的事业来的。在调车员被两个车体的连接车钩挤压致死 的那个事故现场,谭连民、杨启才他们有柔肠,有悲痛,有止不住眼泪,因此才答应了调车员在他生命的最后提出的可怜要求。谭连民当时是有所犹豫的,因为他知 道把调车员的农村妻子调进车站的权力不在他们手上,他想到了调入的难度,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是杨启才抢过话来说:“我们答应你,不管有多大难度,我们当着 现场的这些职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把你妻子调进车站来的,你放心吧。”杨启才在关键时候能够坚强地站出来,并能做出这么大的保证,这也激动了谭连民,他 也说,“书记和我宁可不当这个官,也会对得起你。”分局果然拒绝了他们对死人的这种允诺,但是他们不能欺骗死人,不屈不挠地做到了不对死人违约。谭连民、 杨启才两位是心里装有弱者的苦痛,并因此敢“为民请命”的人物。《大站》因为有了对这两个人物的深刻性塑造,颇具感动人之心灵的文学力量。
《大站》、《在路上》、《纪委故事》以不同角度展现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市场经济成为铁的法则的氛围中,昔日计划经济培育的铁路企业--“铁老 大”,早已风光不再,使得这些当年的天之骄子们焦头烂额。在社会的剧烈转型中,铁路等国企面临着阵痛。在生产关系重组、利益错位的的特殊情境下,人们的思 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发生的惊人嬗变。他们每天面对的是如何落实上面的刚性下岗减员指标,必须解决的是月月拖欠的工人工资问题,倾力应付的是四面八 方伸过来的利益之手,时时关注的是明争暗斗的权利角逐,真正用来抓生产、搞经营的精力,已经所剩无几了。读者看到作家冷峻地叙述——工人们声泪俱下地请求 留岗,心情复杂地参加考试,欣喜若狂地签领工资,怒火中烧地掀砸汽车,乃至因为不正之风横行,段长也落得挂印辞官的时候,读者既为他们所遭遇的生活困窘所 震撼,也为作家对底层真髓的逼近所震撼。真实地描写出生活的实际,给时代留下真实的影像,是作家责无旁贷的职责。阅读张力的一系列作品,可以窥探到张力对 自己创作的文化语境的定位。张力作品中的“铁路情结”形成了清晰而系统的创作追求,“我写铁路生活,对它的作用不敢妄想,但我估计人读了这些文字后,大约 可以得出一个印象,铁路是以圆的曲线来构建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圆,是地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后者才是张力创作的要旨所在。《说文》之意,圆, 全也。《吕览审时》说,圆乃丰满也。《康熙字典》说,圆即圆满、周全、完备等之意。铁路生活“是圆形”之意,首先正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张力作品的精神世界 与地域文化进行打通和对接。张力以自己的创作建造着地域文化场。换而言之,张力作品中的铁路生活,是整个城市文化的缩影。如此一来,铁路生活已经不是地域 性的,而是城市文明的符号话语。
在很大程度上,张力没有过多地强调城市生活以及铁路企业地域性的文化差异,我们感受到的是地域文化的一点一滴。他的一部部作品如同一条条小河流向大 海,以集聚似的方法汇拢地域文化的精要。细读他的作品,读者很容易发现,张力所描述的城市生活风俗人情,产生一滴水见太阳之功效,有着现代诗情浓重的色 彩。张力引领读者进入的是地域文化的大语境。这也是张力城市生活以及铁路企业生活场景地域性创作的本质所在。当读者由此进入张力的作品,就会深切感受到他 的博大,触摸到现代文化的温暖与潮湿。
仅仅写出城市生活的外观,那只是照相师的功能,真正的作家是揭示生活与发现,给予读者以更深层次哲理的启迪。张力作品在描摹原生态生活真实的同时,揭 示了人们习焉不察但却令人触目惊心的“第三种现实”:道义的溃败和灵魂的蜕变。在张力小说中,作家虽然没有写出亟待绳之以法的腐败分子,但却尖锐地揭示了 弥漫成风的腐败现象,给人以鞭策、警醒和感悟。惩治一个腐败分子不是难事,扭转社会风气则非易事;一时的腐败可以根除,见惯不惊的腐败则最令人担忧;腐败 的伎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腐败的伎俩被当作人生智慧而高扬;可怕的是在腐败面前,社会的正义熟视无睹,人们的良知置若罔闻!张力小说最令人激赏之处,振聋 发聩的发现和某些反映铁路部门、工业战线改革或反腐小说相比较,张力对这类题材思考的深刻和独到。《在路上》中的段长孟宪伟,他的成功和失败,他的辉煌和 颓唐,他的过关斩将、败走麦城,但令人悲哀的则是在腐败气息的氤氲中,大家都乐陶陶地、前赴后继地随波逐流!张力在铁路改革题材之外,有着同样意蕴指向的 《法律援助》、《纪委故事》和《加减乘除》等也是这样。《法律援助》中母女两代人的悲苦命运,是谁之罪?难道光是人贩子恶意所为,执法不严是祸根?《纪委 故事》中的纪委书记倪文古,本来自负个人的能力水平和工作业绩,谁想到他升迁的背后,还有着同学提携的暗箱操作?本来以为审理纪检案件是职权范围内的正常 工作,哪里想到正常工作还要曲线救国、暗度陈仓?当一切正常的工作都需要非正常的手段进行时,读者欲哭无泪了。至于《加减乘除》中围绕着新任副院长的选拔 所发生的那些闹剧,人们也似乎是司空见惯,但透过作家亦庄亦谐的叙述,对这道加减乘除的简单算式,就是智商可怜的低能儿,也能够知道它的可悲答案!张力绝 不只是在展示围城中新儒林的众生相,他是以此传导深长的忧思:薛荣这类庸才坐收的渔翁之利,将给我们的干部队伍带来什么冲击?而公仆队伍中多了薛荣们的弹 冠相庆者,是否折射出我们的选人机制出了什么毛病呢?
《家在远方》、《两个人的车站》、《一隅苍生》、《走进歌厅》,这小说的名字本身,就透发出一种漂泊与苍凉。古人有“圆而神,方以智”之说,其中圆指 行为处事所谓的“通、活、融、满”,神即“神、通、广、大”的宇宙观。赋予方圆思辩的哲学意象。圆与圆形结构在文化意境深层结构中包涵了丰富的哲理和品味 不尽的巨大思辨内涵。朱熹《太极图说解》说,“○者,无极而太极也”。他说,太极只是一个浑沌的道理。“浑沌”正是圆形的一种状态。正是这种久远的圆形崇 拜,发展形成了一种“圆文化”。人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力求归趋于“圆合”,追求一种圆满无缺的境界。清代褚人获在其《坚瓠余集》的卷一《赵歧解圆字》中 曰:“惟圆则无障碍,故曰圆通;惟圆则无爲缺,故曰圆满;惟圆其机尝活变化出焉,故曰圆转,又曰圆融。”有关圆的这些意象,张力的作品就是对圆文化的注 解。他的创作实践也是一个圆,以城市文化为核心,一切围绕这一核心运行。每一次的创作从起点到终点,而终点又是下一个注解的起点,周而复始。圆形文化,成 为张力文本世界的灵魂和骨架。
《家在远方》集中地体现了张力小人物的悲歌。走出家乡大山的朱永禄,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朱永禄走出大山,是为了谋生,虽然与现代的交通铁路结缘, 面对着色彩缤纷的精彩世界,却永远无奈,次次与幸运失之交臂。朱永禄的质朴憨厚,他那独特的处世哲学,赋予他简单的顺向的思维定势,使他在爱情、工作、升 迁、事业上一败涂地。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的中专生朱永禄,这位当年学校里人人敬重的大班长,到头来,连自己的干部身份都丢掉了,在外面打拼数年后还是落魄 地回到了原点,连自己的家都不知在何方。张力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中专生朱永禄其实是一个站在明处的窥视者。生活者与窥视者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 阵营,原本在学校里还算可以的朱永禄,来到铁路,却不幸成了弱者,《家在远方》作品的结尾:“伴着一声沉重的叹息声,两颗硕大的泪珠滚出他浑浊的双眼”, 读者面对世事如棋局,不禁潸然泪下。对朱永禄的人生命运的感叹之中,可以领悟到生活的真谛。
《两个人的车站》茫茫草原深处的新线小站小李和老胡,生活中满是荒凉和寂寞。两个人创造了爱情神话。靠着爱情的精神支撑,他们给生活增添了希望,熬过 了一个个寂寥的日子,保证了草原列车的安全运行。当那美丽的神话被冷峻的现实撕破的时候,读者的内心真是打翻了五味瓶。为了铁路建设,小李和老胡们付出的 真是太多了。而铁路企业,正是由于他们的忠于职守才鹏程万里、迅速腾飞。小李和老胡这些普通工人,虽然没有经天纬地的贡献,被人看做是一棵无足轻重的小 草,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铁路企业不会忘记他们。每个平凡的铁路工人都是遮蔽风雨的一棵树!
当年作家谌容一篇《人到中年》曾经震撼文坛。张力发表在《中国作家》的头题小说《一隅苍生》与《人到中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林立德医生这个柔弱的江 南书生,义无反顾扎根北国山村,缺医少药的农村没有助产士,林立德用自己的双手,几十年不知将多少婴儿平安接到了人间;他给这里的一隅苍生带来了幸福和文 明。世俗偏见将林立德这个男助产医生打入另册,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着他。小说深刻的批判性,启迪人们对愚昧的国民性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白衣天使林立 德的艺术形象,是当代的陆文婷,具有忧国忧民、抗击世俗的反潮流勇气。林立德与陆文婷同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是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商品 大潮之中,守望理想的林立德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有着文化自觉意识的张力,在还原城市文化图景的过程中,思考着当代文化的价值和命运。张力的所有文本皆为城市文化最具代表性那部分的凝结,是极为自觉 的行为结果。张力在建构和挖掘地域文化时,更多的时候,是在互动性的比较中进行,在对抗甚至是毁灭中,回望城市文化的价值。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精神是持续的精神:每一件作品都是对前面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走进歌厅》结构布局缜密, 视野开阔而细腻,语言精致而流畅,内涵丰厚,张力扫描了另类群体在大都市的生存态势,直击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外在形式,内在营构;无论是人 物谱系,还是风尚意象;与以往的作品一脉相承,构成了一个系统。一路走来,灯红酒绿的都市夜晚,色彩缤纷的歌厅群体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张力笔下的小姐温情 脉脉、异常鲜活,其叙事更多地指向文化意义。张力以非常的独特视角,透过高耸楼群、车水马龙的街道,将笔触深入到这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作家的叙述笔调温 婉,读者得到的感受却极其复杂,阅读的冲动极其迫切。张力柔韧犀利地撕破这讳莫如深的遮蔽,揭示这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对歌厅族的精神层面进行了剖析。歌 厅是社会细胞,张力透过这个视角来观照底层世界,即便是纯洁的豆蔻少女,也不得不服从生活的潜法则。破译作家的创作意旨: 密切关注社会生活,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日本进步作家川端康成的许多作品,早已涉及了歌女这一社会角落,《雪国》、《千纸鹤》等等莫不如此。张力的小 说在反映生活深度的同时,更着力于对人生价值与生存与发展图景的描绘,显得更有意义。
张力出生和成长在锦州市,自然深受此地民间文化的滋养。张力充分利用了这样的馈赠,锦州是张力创作的灵魂生发地和精神意象场。 锦州作为张力个人的故乡已经被他置换成一个民族的家园,他对锦州故乡的那份依恋和追忆拓展为文化乡愁。张力处于地域之中,又跳出地域观照整个民族的生存境 界。锦州市临山面海,张力不是一味的固守,做虔诚的开掘者和解读者。而是深刻意识到传统文化所遭遇的挑战,理解走向现代意识的渴望,并着力图解这样的裂 变,以此实现主体的文化建构策略和立场,推动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文明的优化发展。在这样的现代性冲突中,张力努力让生命行动上升为一种文化行动。 他以自觉的区域文化意识进行的审美诉求,建构了张力的文学审美场域。
与其说张力行走于锦州地域文化深处,还不如说他怀揣锦州地域文化行走在阳光下。张力以锦州市为轴心,辐射面广,随时可以走向海洋,随时可以走向北京, 随时可以回到原点。张力是锦州地域文化的生命载体,又是走出锦州地域文化的守望者。他来自于平民阶层,又始终葆有平民情怀,张力关注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平 民,写的也都是平民生活。张力将平民的身份带到写作状态之中,让自己一直作为平民而写作,是张力一贯的创作追求和创作体现。他的所有作品,都深蕴浓醇质实 而清朴真诚的平民意识,显示了他是一位具有独立主体精神的作家。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进入精神世界的方式,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他的姿 态,他的叙述,他的精神内质,都是平民化的。他以平民的身份,处于平民的立场,以平民的眼光和心灵打量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状写平民的生存状态、文化人格 和饱满人性。一以贯之的创作理想和文本世界强烈的平民化气息,使张力在当代作家中极具个性气质。而他的创作,又如平民一样,看似平常无奇,无树大招风之外 表,却有丰足的内蕴和能量。在当下社会,张力沉住了气,抵制住了社会上的诱惑,他在慢慢用心灵去写作,像园丁一样不事张扬,精心伺弄着自己的花圃。张力的 小说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多样,锦州市同乡、现实主义作家孙春平的提携和辅导,对张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锲而不舍的20多年艰苦奋斗,张力度过了艰难的探 索期,走出千廻百萦的围城,拼搏出文学艺术的自己的一片天。
福克纳说过“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 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而对于当代中国作家而言,与其说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还不如说是福克纳的效仿者。陈忠实的白鹿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莫言的高密 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等,业已成为文学作品中作家的独立王国。张力此种文学的自觉意识更为浓郁,在创作中营建着文化的整体构想和诉求,是他生命的必然选 择。张力立于一个更高的文化地标,去看待城市文化内涵,继而舒展更大的文化雄心,得益于他的强烈的文化意识和使命感。是成功的叙事与形而上的思考的有机融 汇。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对文化的深度体悟,使张力用心关注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在歌颂中坚守,在批判中重建。他以植根于人类大地的人 文精神,对世界、对人、对“存在”与“在”作出深刻思考与回答,对民族生存状态、自我存在意义、存在方式、现实图景关注等倾入了平民的悲悯的人文关怀。但 张力就是要在这绝望之上建立起自己的人文精神支点,坚守着作家的良知,承担着作家的使命。作品始终避免格式化,具备不确定性,表明张力思索总是在路上,与 生活的对话一直进行着。张力的作品,传统的话语与现代小说手法的有机结合。传统文化叙事的根本点在于寻觅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并从一开始就坚定了自己的文化 理想。张力知晓传统文化是民族立命之本,其强烈的生命力是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是在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在吸纳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中壮实,只是要正本清源, 坚守经典,而非彻底颠覆或本末倒置。
张力创作的几篇官场小说,社会反映很高,多被转载,还被多家的选本收入。为此张力多了几分信心,写的官场小说便也多了起来,官场及准官场小说陆续发了三十几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了《世纪大提速》、作家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发了《官殇》等官场的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官殇》是张力倾心打造的现实题材作品。张力在市公安局挂职期间,曾经经历的一个案件,某企业官员被打劫后,不敢声张报案,造成了案情的曲折 复杂,从侦察到破案,从官员到百姓,纵横交错,如此一搅和,便把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官场”便自然走入到了社会的一些角落里,让人觉得这 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加之张力用小说语言和技术上的操作,让官场无法遁形,轻而易举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谁都知道,作家写长篇小说一定要好看, 张力认为,就是故事结构要鲜明,一环扣一环,细节的真实刻画,这需要大规模的信息量。在《官殇》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奇妙穿插了各种情感的交融,抢劫案给 相关人直接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触动了人情、亲情、感情、恋情的裂变,为此长篇小说涂上一浓重的感情色彩。《官殇》案中有案、扑朔迷离,人物刻画鲜明、个性 鲜活,故事错综复杂、高潮迭起、跌宕有序,情节合情合理,撼天动地,感人至深。中国某报发表文章评价《官殇》:“这部即是公安侦破推理又是反腐倡廉大题材 的长篇小说,能写得如此娴熟,也能看出作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这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张力为了创作《官殇》这部长篇小说,阅读了张平的《十面埋伏》,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成功的《黑洞》、《黑冰》、《黑雾》,张宏森的《大法官》, 胡玥的《危机四伏》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张力认为,其实在《国画》之前,从长篇小说《新星》开始,官场小说诞生了。随着《新星》同名的电视剧热播,呈现出万 人空巷之势,县委书记周里京的形象深入人心,那时的这种主旋律的小说不胜枚举。可现在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提到官场就是腐败,就是堕落,这样难免偏颇,真正 的官场小说,应该倡导正面的积极意义的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力的长篇小说《世纪大提速》,就是具有主旋律的,也算官场的长篇小说。但其归类应该算 作法制文学里的长篇小说。张力喜欢法制小说,也侧重这方面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他在公安局挂职体验生活的初衷。《官殇》从某种角度,又应该是一部法制文 学,如报刊评价《官殇》“即是公安侦破推理又是反腐倡廉大题材的长篇小说”,近期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力长篇小说《政绩工程》,以及张力刚刚完稿的 长篇小说《法律援助》均为法制文学。官场的腐败,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就会报复仇杀丧心病狂,而出现的结果就会与“黑”发生一些关 系,就要牵扯到司法,就要引发司法(亦为官场)的腐败,而司法的腐败将更为可怕,《官殇》也涉及到了司法腐败问题。张力极其注意在创作之中,着重体现文学 性。张力十分欣赏放羊老人的一段话,老人说“钱有啥好挣的?钱那东西,一催命,二折寿,让人坐不住躺不下,趔趔趄趄地往前爬,太阳晒一天,我老汉明白一 天,谁想找不自在,谁就去奔大钱。”这平凡的话语出自放羊老人之口,真是发人深省啊!
张力的创作,对二十世纪和新世纪锦州市文化界多元化文化挟裹下的人性走向的研析,是有深度和力度的;因为深入了历史,融入当下语境,心灵始终在场,而 直抵人性和社会深处。他真诚面对内心的巨大焦虑,不回避民族发展的忧思和人类生存的漩涡,批判中既有黄钟大吕,又有脉脉温情,使他的话语更具力量。“文章 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阅读张力的《大站》、《在路上》、《纪委故事》、《世纪大提速》、《官殇》等等小说,饱满的元气,桀骜的灵魂,温柔的表达,让你在 阅读中,亲历着非凡的精神冒险,并在这种冒险中获得心灵的宁静……,读书让人年轻,让人感慨,让人意气风发,属于所有寻觅真理,渴望安详的人。应当说,张 力的作品是一个内蕴极其丰厚的寓言世界,值得读者细细品读。
|
|


 首页
首页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 新闻资讯
新闻资讯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 监管履职
监管履职 互动交流
互动交流 网上办事
网上办事 专题专栏
专题专栏






 京公网安备 11040102700028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102700028号


